读书笔记,《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摘抄
作者: 陶希圣 发表日期: 2024-12-08
读后感
陈丹青的推荐书单。
陶希圣先为蒋介石工作,再投靠汪精卫从事卖国工作。所谓潮流、点滴,即在民族统一的大潮流中迷失了自我,对于汉奸工作点滴不提。 如果汪精卫百分百汉奸,高宗武、陶希圣至少有60%汉奸成份。
不知为何陈丹青多次提及这俩?
注:文末补充了陶希圣为大汉奸汪精卫工作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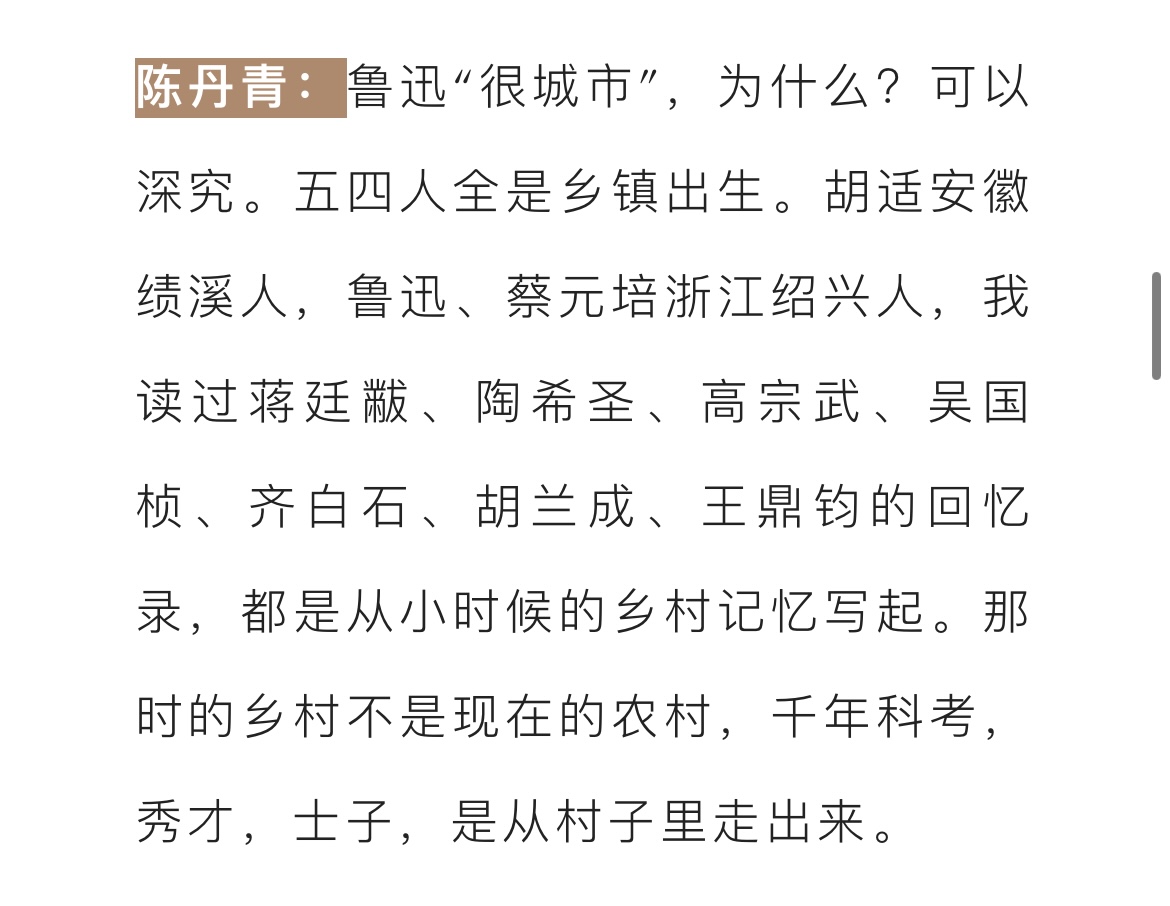
推荐指数 *
生活态度
但是我们总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青年人应该辛勤劳作,今天苦一点,日后必将有好转的一日。 只有一次,也只有那一次,冰如埋怨我,不该拿大半薪水去买书。她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
我答道:〝我总不能在商务印书馆过一辈子。我要因上进。”从此以后,冰如不再说一句埋怨的话。 我总以为社会有公道,不会亏待一个努力上进的人。只问自己有无学识,断乎不可为了生活一时清苦而怨天尤人。
清苦的生活乃是人生的磨炼。一块生铁,要干锤百炼,才变成钢。
我以为人生永远要虚心,不断求进步。我深信治学要由博反约,好学深思。我深信做学问要虚心,留心,用心。 一般人总是“文章是自己的好”,我是相反的。在我的眼光中,别人的文章,都有他的长处。我不轻视任何人的文章。
我觉得自己的文章每一篇都不能满意。 仿佛行路,目的地是在远处,次不半路停留,必领全心全意全力向前进,不到达目的地不止。
中国人特点
依中国民情,死亡可使弱者突然变大,活人总是理屈三分。我们倒是都懂,都抓住了机会。闹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总觉得欠王吉林一点什么。 也许我们利用他多于同情他。后来我 知道,学潮无论多么波澜壮阔,大抵不出这样的框架。
中国人最忌“撕破脸”,整人用阴功,表面照常君君臣臣,一旦公开決裂,难以善了。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们就自暴自弃了。
山东有句俗语:“一个牛也是放,两个牛也是放”,意思和“—不做,二不休”相当,一旦越过这个门槛,我们就是浪子。
三十而立
阴历正月初四日,派人去接冰如回来。次日清晨五时,我们同到母亲床边告别。一家人只有我的三姐起来相送到大门。
其余的人们一律不理会。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拿走。
冰如的首饰与陪嫁的衣服布匹,更不敢带走。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
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飘泊之人, 只有努力向前撞。
生活一瞥
我记得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鼓楼街新开一家洋货店,叫做“华胜公司”。全城为之哄动,大家去看热闹 我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东洋车)说“到华胜公司去”。那车夫把我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去。我找不着那公司,就回来了。
我还记得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穌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法律老师
生:“你把全部讲义都划进要考的范围了,请你减少。”
我:“我不是卖菜的,讲斤两,讲价钱。”
生:“你们北京大学考试都划范围,你有什么理由不划?”
我:“是的。北大的先生有划的,也有不划的。”
生:“划怎样?不划又怎样?”
我:“划范围考试的功课,我学不好。不划的我学好了。在校时,我骂那不划范围的先生。出校后,我骂那划范围的。”
生:“你现在怎样?”
我:“我宁可让你们现在骂我一顿,不能叫你们出校之后骂我一世。”
学生们说:“说他不过,走吧。”
教书生活
这一学期,是我教书生活上最为愉快的一个时期。法政专门校址在百子亭,那是一座公园,虽无奇花异草,而有林泉清朗之胜。每日课余,晚饭之后,将近黄昏时候,伯猷与我并肩散步,一小时后,各回宿舍,找材料,编讲义,并预备明天的功课。
每星期日,法专与第一中学两处的友人集会于迎江楼(茶馆),或大观亭(名胜)聚餐。法专有曾伯猷、冯若飞、胡幼吾和我,—中有易君左、郁达夫诸人。在这中间,君左是一个中心人物。每次聚餐,非他参加即缺少兴味。
郁达大携书他的元配太太到安庆。他对那个乡下姑娘很是亲爱。比如他在星期日上年出门访友,到十二点。而迎江楼聚餐是十二点半,他定要回家打一转,再到聚餐的处所。
从学校到工作,放现在也差不多 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
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
从手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海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
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
民主人士
黄炎培那一套“悲天悯人”的神气,一口气说完他到首都来见了委员长以及孔院长、何部长,还有一连串的会谈,仿佛一家大照相馆的玻璃窗一样,陈列着军政大员的相片。
人生不可赌气
壁报叫座,我意犹未尽,又把《悼王吉林同学!》奇到安康,在《兴安日报》副刊发表。这可是我第一次跟人赌气。几十年后,我才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看到一句话:人生什么都可以赌,不可赌气。
战略打战略
蒋委员长对我们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七七事变,胡适之态度
到了夜半,才知道蒋委员长在西安蒙难的消息,也就知道旧学联这次游行的目的何在了。
冀察政治分会宋主席明轩宣告病假。北平各界惶惶然不知所措。北京大学教授们在王府井大街新开的丰泽园聚餐。
胡适之先生对我说:"你们国民觉有人。国民政府领发讨伐令,证明了 国民党有人。有的是读书人。我一向反对国民觉,今天我要加人。
抗日靠山,反共靠水
今天查地图,在这一条线上有许多大山,国军利用山地作战,拖住日军。这条线上有山西的吕梁山、中条山,河南的伏牛山,湖北的鄂西山地,湖南的湘东山地,广东的大庾岭和云开大山,广西的南岭和十万大山。
中国的山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山是老天预设的防御阵地,人挡不住的、山来挡,后来有句话,说是“抗日靠山”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又有三年内战,共军破坏陆上交通,国军主要中海上运输支援,因而出现了下一句话“反共靠水”,此是后话。
那时有几千万中国人,被日军压缩到黎东方所说的长线之西。战争期间,无论如何这些人总有同舟共济的心情,说个比喻,大家像在寁夜围着一堆火,利害相同,心念相近。
三个自觉
上海大学的大门之外,设有一小书店,名为“上海书店。发行上海大学的讲义和小册子,其中有瞿秋白编译的《社会科学概论》,分册陆续印行。
实际上,他的底本是布哈林的《唯物 史观»。据说中国共产觉自民国九年发起,十一年成立,直至翟秋白从莫斯科回国,才知道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我到上海大学上课之余,亦购买此类小册子回家浏览。 国家主义派是反共的,由于反共亦即反对中国国民党容共。《独立青年》与《独立评论》对于共产主义有学理的批评。
我在《独立评论》明白标榜三个自快,即“民族自决”,“国民自央”与“劳工自决”。所谓民族自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股潮流,也就是民族主义的一项运动。所谓国民自决就是民主主义。所谓劳工自决是主张劳工的利益应由劳工自己组织的工会努力拿取和维护,而反对布尔什维克所调职业革命家利用无产阶级的名义作政治斗争。质言之劳工自决就是工会主义。民族自决是与国家主义有别的。劳工自决是与共产主义冲突 的。我接到环龙路中国国民党党部的信认为,《独立评论》的三不自觉是与三民主义相契合。
训政与宪政
“毛泽东一月十四日时局声明的八条,显然是招降而不是言和。李代总统一朝视事,即发表声明,接受其为和谈基础。
在党内末经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政府亦未经行政院,遽然决定和发 表。孙院长何以对立法院负责?这不是明白的事实吗?
问:“盛传南京方面希望蒋总裁出国游历,此事如何?”
答:总裁领导国民革命,经北伐与抗战,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并且结束了训政,开始了宪政。在宪法上,人民有居住的自由。三十年统一国家的革命领袖,如今引退返乡,就失去了居住故乡的白由么?
中国社会阶级观点
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
我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偶然发表一篇短文,指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是以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为主要阶层。 短文对于土大夫阶级的发生、发展与没落,作简明的分析。
这篇短文引起友人的激赏,同时也引起左右两端的批判。
五四之前的文学和史学以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为首脑,至此已经是最保守的一环。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的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
但是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个问题 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
共产党的干部派认为中国社会不过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派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如中国大学教授黄松龄就是干部派份子,马哲民附和干部派。
反之,刘侃元是倾向反对派的,施复亮是附和反对派的。他们都在中国大学讲课。但是北平大学法学院乃至朝阳大学的学生也随时请他们演讲。
当某一大学的学生团体邀请某一位先生演讲的时候,那位先生生上了讲合,若是提起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反对派的学生立刻跺地板、搥桌子,表示昇议。
若是他一开口,就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干部派学生也作同样的反对表示。
阶级与阶层
共产党处处讲“阶级”,主任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
这个说法吓人一跳,阶级好比楼梯,下面的一层还可以伸出头来透口气,阶层简直是水成岩,上面盖得严丝合缝,不见天日。想用阶层代替阶级,弄巧成拙啊!
第二个挫折是签订中苏友好条约。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依条约规定,外蒙独立,东北的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由两国共管。中国损失重大,新闻界称这个条约对中国“割去一块肉,抽掉两根筋” “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中共及其同路人的批评与攻击,纷至沓来。党中与政府领导同志向委员长陈述一种意见,以为本书引起激烈的批评,殊非始料所及。
又有一种意见,以为本书以始即不应出版。委员长答道:“我写了一本书,若是没有强烈的反响,那才是失败。”这就是著者对待本书批评的态度。
我说:“我们国民党籍参政党员人数虽多,其组织远不如你们那样严密,因此我们的党决无操纵参政会之事。”
他们表示这话不可信。我说:“中国国民党是全民的党,对于各种思想和主 张,只要是革命抗战的,都可兼容并包。
党内与党外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我们这一缺点亦就是我们的优点。一个党如过分狭隘,所得不偿所失。”我的结论是希望中共参政员以民主风度,在会议中辩论一切问题。
在会议中,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周恩来等采取谦和而坚定的态度,以博取各方的同情。反之,那些左倾如救国会诸人,却从事斗争。
民主
中央政府机关向武汉区重庆疏散。国防参议会随着交通都专轮迁往武汉。罗钧任(文干,先生与我一同在官舱的客厅里打地铺。
一路上,长江的上空是凄风苦丽。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断不寂寞。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钓儒等常起争议。
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
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用,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他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我说:“世交是世交,舞 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他说:“那又何必!”说完后,相对而笑。
民主人士
十二月十二日之前三天,左派分子筹划游行集会,庆祝“双十二”。
他们是借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鼓吹“民主联合政府”。我在国防参议会提出这件事。黄炎培又拿出他“悲天悯人”的腔 调,说道:“万万不可这样,我一定去找童必武谈谈。”
董必武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年的驻京代表,此刻在武汉。沈、黄诸人是经常奔走于政府与童之间的。
黄炎培说话之后,我起立发言:“董必武对人说:只怕国民党不开门。只要它的门开一条缝,我们便挤进去。门缝挤开了,我们便撞进去。门撞开丁,我们便打进去。你们诸位与他谈什么〞
沈说道:“董先生真说了这话吗,不可信。”
关于绝对服从
要一个人绝对服从、完全忘我,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领导者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他本人确己以身作则、彻底奉献给大家共同服膺的抽象理念。
基督教的对象是神,问题较少,至于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的政治人物?上帝并未创造这样的人 类,群众者以此期待领袖,乃是逆天行事。
事实是,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权自肥。 所以要求“绝对服从”,政府与人民可以虑始,难与乐成,聪明人阳奉阴 违,纯洁的人就愤世嫉俗了。
服从!服从!代价何其沉重!抗战救国要每个人付代价,付很大的代价,可惜由于专制,可以任意挥霍,不肯精打细算。有多少人,抗战不需要他们死,他们死了,不需要他们残,他们残了,不需要他们破家,他们赤贫了。
除了敌人的残忍,这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为了抗战应该人人吃苦,于是不再关怀别人的苦,甚至安心制浩 别人的苦。
所以,我说过,“抗战!抗战!你是我们的骄做,也是我们的隐痛。 “纪对服从,的理论终于破产,在二十二中,因西迁而破产,在全国,因胜利接收而破产。
与胡适之
有人误解我是胡适之派。其实,我和他在治学方法与讲学精神上,大不相同。北京大学这时包容着各种学派和学说,而章太炎先生学派有些教授是向左翼靠拢了。
在国难中间,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胡适先生是与我们的党站在一起。
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末必大乱”等失败主义的论调。这些论调得到了江精卫的赞同。
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定认识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宣传我们的主张。
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
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还渐传出,渐渐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我们毫不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困体,叫做-低调俱乐部’。而且这个“雅号,还是胡适博士给起的。”
把我们这个小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这个雅号是胡适博士给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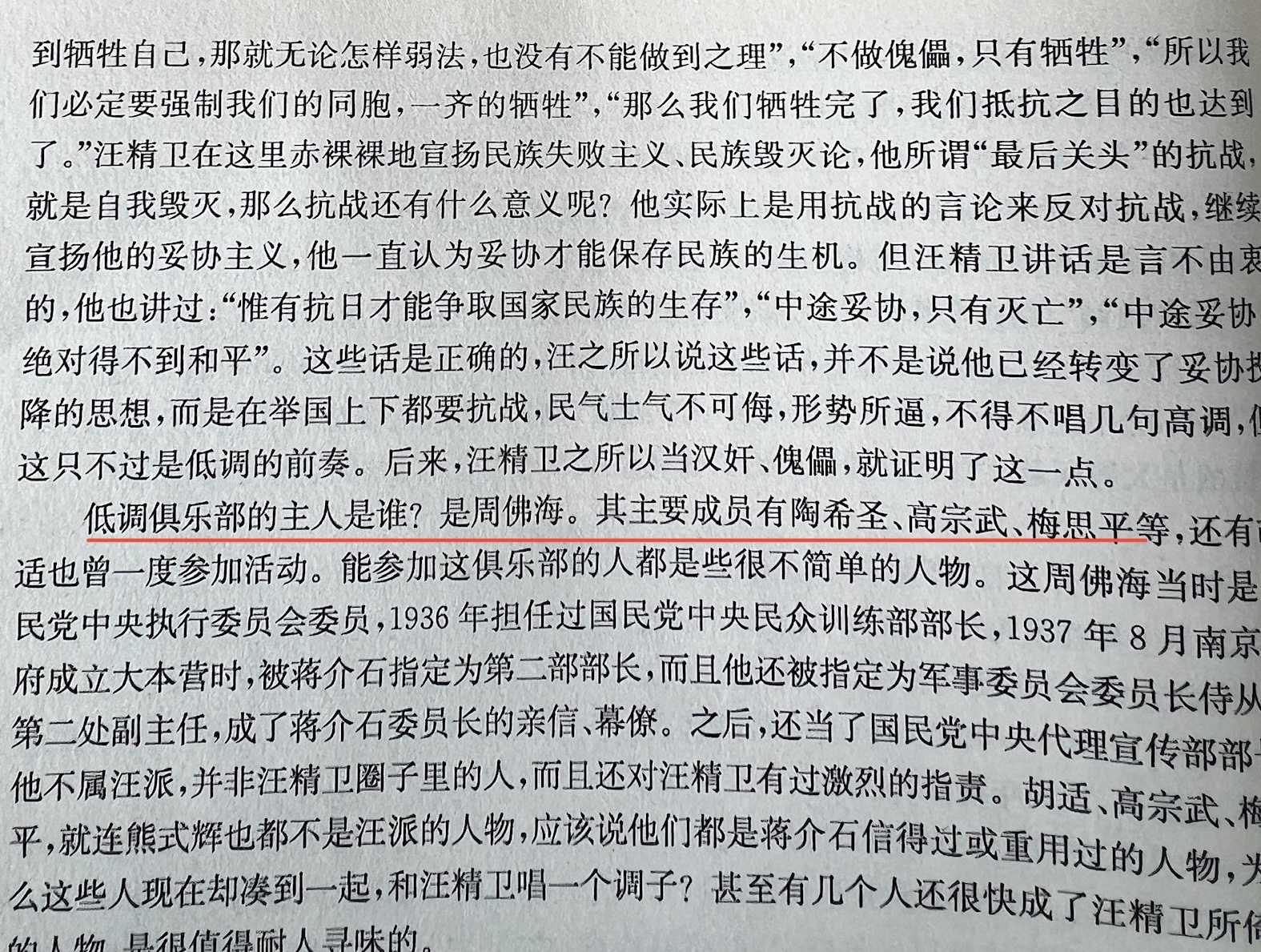
与日和谈
1938年12月初,周佛海和陶希圣先行前往越南河内,周佛海以视察工作为名,陶希圣借口讲学。他们在此等候汪精卫的到来,寻求与日本方面的和谈机会。

三奸开会
汪记“六全大会”开过后,汪精卫认为在此基础上由他来组织“国民政府”,于法有据了。
在日本机关长影佐祯昭的怂恿下,在日军的戒备下,江精卫率周优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怪等由上海到南京与梁鸿志、王克敏就组织“国民政府”问题进行磋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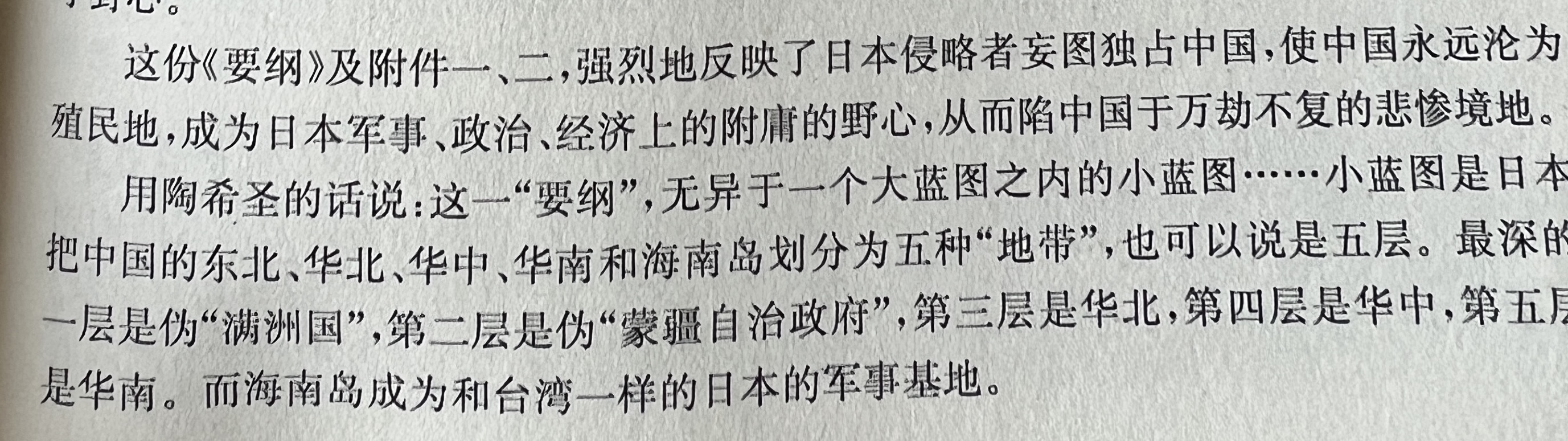
最高委员会

投日方案
“以到东京的第二天上午起,我与影佐先生连续会谈五天。日本政府对汪主席提出的关于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和安现中日和平的方案,完全同意。”
高宗武将与影佐会谈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一遍。汪精卫提出的投降方案是:
一、由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重建新军,组编12个师的军队;二、三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他将再饮发表声明:
宣布在10月10日,组织新政府;三、向日本贷款2亿元;四、进一步轰炸重庆,直到彻底摧毁重庆国民党政府为止。

高陶事件
来源《高宗武回忆录》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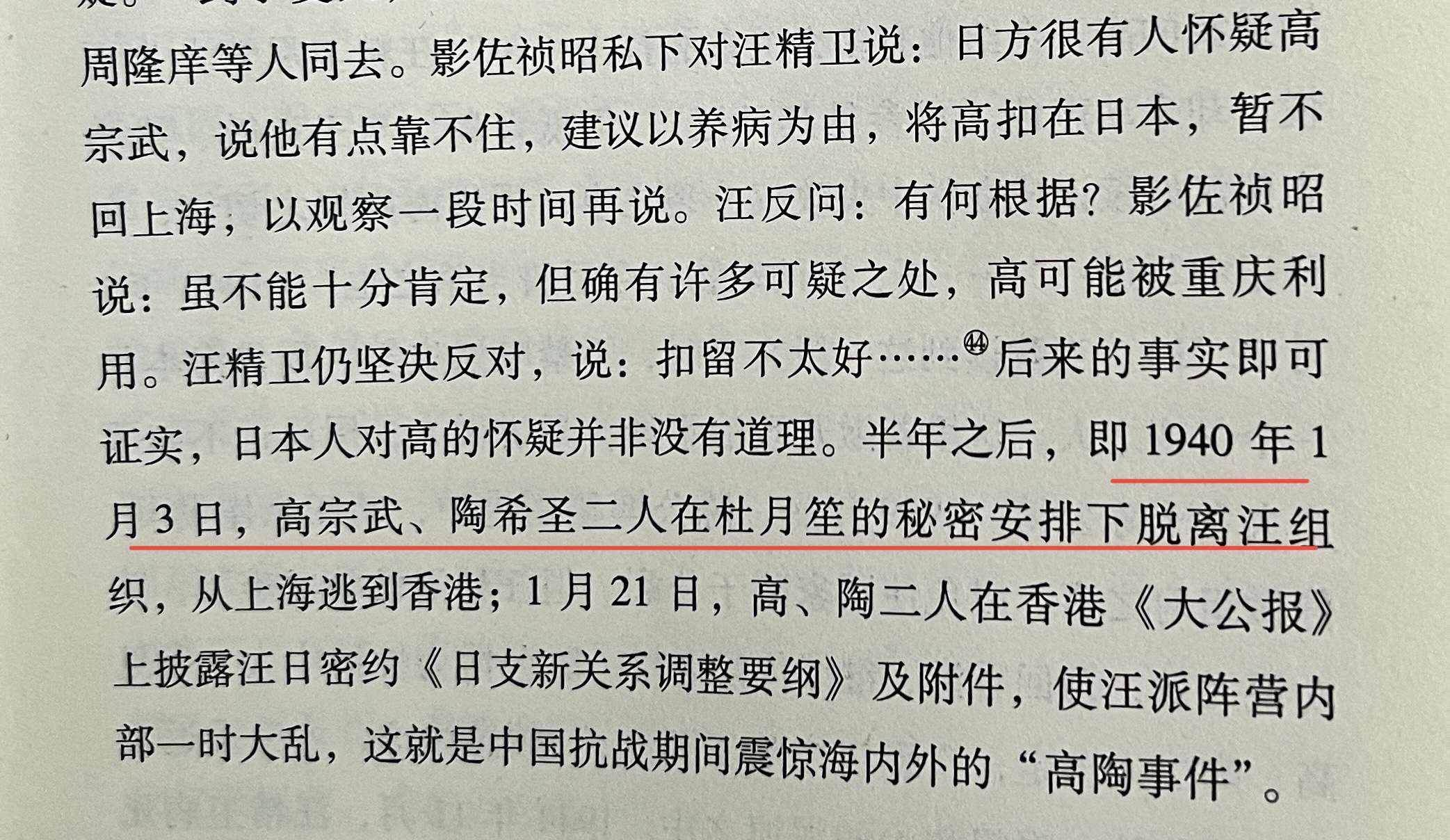
来源《汪精卫大传》序,图1
高陶出走原因,分赃不匀
高、陶事件是汉奸集团中的一次内江,是争权夺利达到自热化的尖镜表现,是分赃不均的必然结果。
按照罗君强的说法:陶希圣这次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海之下,自己仅得一席常委兼宣传部长,听说周佛海又将掌握伪府财经大权,更是因羡生妒。 自命一介书生,当个冷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向汪精卫有所表示。哪知汪已将教育部长给了当时所渭无党派人士赵正平。
陶抑都,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个名堂来,只好再动别的脑筋。

高宗武
